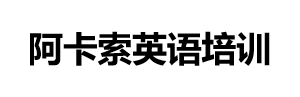那些艰难的学习外语的岁月
编者按:《废墟曾经的辉煌》是著名小说家张陵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 这是他20多年散文创作的集锦。 张玲出生于沿海城市温州,童年生活在瓯江畔。 后来,她离开家乡到上海上大学,然后离开中国漂流到大洋彼岸,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她渐行渐远,远离家乡,她在异乡写家乡,字里行间都带着浓浓的乡愁。 江南风情。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恐惧是我永远无法克服的,比如开车,爬山,在人群中认出一张脸,或者在晚宴上遇到一个表情严肃,无法用言语刺穿一个字的人。锥子。 近邻,或者天花板上挂着一只蜘蛛,尤其是一只鼓着绿色肚子的蜘蛛……我的恐惧是无数的。 但总有那么一两件事让我感到无所畏惧和坦然,比如学习不熟悉的方言甚至外语。 我用这两件事来抵消我对世界的整体恐惧,并用它们来维持我生存所需的平衡。
我的家乡以其独特的方言而闻名全国。 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根据口音立即识别出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 在我的童年甚至青少年时期,普通话还没有流行。 我们称街上行走的少数讲普通话的人为“外地人”——这个称谓带有明显的蔑视。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歧视。 。 我上的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 班上有几个南下的干部子弟。 他们不会说温州话。 我们的耳朵和眼睛就像井底之蛙,他们说的是“大舌头”普通话。 没过多久,我像流感一样感染了他们的“大舌头”,被老师选为一些季节性诗歌朗诵节目的表演者。 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脱离顽固的地方口音,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另一个发音环境也是一种技巧。 这项技能的基本秘诀是:大量的无畏甚至大胆,加上等量的喜爱,再加上一点天赋。
当我十六岁时学英语有哪些困难,我辍学并在郊区的一所小学担任代课老师。 半年后,我进了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车床操作工。 生活无聊,无事可做,于是我开始用大量空闲时间学习中国画。 我成为了一所师范学院美术老师的学生。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任伯年是谁,什么是兼职写作,南派山水画和北派山水画有什么区别等等。当时我学画的动机很简单,实际的。 我想换一份更轻松、更干净的工作,坐在温暖明亮的灯光下,用狼毛画出口制的复活节彩蛋。 但很快我就发现,青春体内积累的能量,并不能被七个任伯年和四十九个彩蛋完全消耗掉。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学英语。 多年后我才发现,这个“突然的惊喜”一点也不突然。 这是我经历了长期的抑郁之后,身体里的一根坚强的神经发出的第一声哭声。 这种突然的突发奇想和学习国画的冲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学英语有哪些困难,我也无意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是一种新鲜事,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之后。 单词。 那时我想学一门外语,只是因为我喜欢探索当地方音之外的奇怪的声音世界。 虽然几年过去了,我的人生轨迹却因此而改变。 这其实是因为世界的突然变化和我最初的动机。 完全无关。
我已经不记得在那个信息极其有限的时代,我是如何得到一本美国制作、香港印刷的《英语九百句》了。 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本书的样子:厚厚的一本书,纸张薄如蝉翼,封面被无数人的手磨得粗糙,很多页都有折痕。 每天晚上我都会躲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那些艰难的学习外语的岁月,把收音机调到最低音量,静静地听《美国之音》,跟着一个叫何丽达的女人一节节课地学“英语900”。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个女人的声音有几分林志玲的韵味。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诠释过任何语言。那声音里有一丝难以言表的魅惑,让我既兴奋又害怕。兴奋是因为史无前例,恐惧是因为害怕惹上麻烦——那时候收听敌方电台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每次听完何丽达的节目,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将收音机调回大家正在听的新闻台。 有一天,我太困了,以至于我忘记了这件事。 第二天,一位邻居过来随意打开我放在桌子上的收音机。 还没听完第一句话,他的脸色就突然变了。 我和他同时去抓把手,他比我快了一秒。 啪的一声,世界陷入了寂静,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彼此脑海中飞驰的思绪。 然后他什么也没说,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任何普通的敲门声都会让我从椅子或床上跳起来。 最终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当我们在院子里相遇时,我们再也无法平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我们都曾是小偷。
当我的好奇心一出现时,何丽达第一个钻了进来。她之后,缝隙变大了,各种各样的人也跟着钻了进来。 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城市里嗡嗡地飞,到处寻找能面对面教我英语的老师。 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上,居然聚集了这么一群陌生的人。 有曾在教会学校任教的教师,有前联合国的退休雇员,有因荒唐而被派到小镇的学者,也有闲散的人。 正式职业之外的私人导师……我崇拜在他们的指导下,贪婪而急切地学习着一点一滴的英语知识。 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他们的英语有一个巨大的逻辑大脑,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句子的组成部分,挑出主语、谓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状语定语; 或者从很长的一段文字中准确地推导出有关动词变位、从句、复杂句型等的句法和语法结论。他们的英语不仅有逻辑思维,而且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可以浏览一页一页的内容。本书一目了然。 但他们的英语没有耳朵和嘴巴,他们患有一定程度的耳聋。

我和他们呆在一起,学到了很多语法知识,这些知识后来会派上用场。 在英国聋哑人的小巷里跌跌撞撞了几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位陌生的上海女人。 这个女人姓周,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和英语系——单是这个背景,就让她在我们这样的小镇上有了一定的光环。 她跟随被划为右派的丈夫,定居在夫家,以私教学生为生。 我每周三次骑自行车去她家,风雨无阻,去上课。 在这里,我用“听”这个词,不是随意的,也不是约定俗成的,我的意思是别的意思,因为她的教学重点是口语训练。 我们(我和她的其他学生)坐在她周围的一个黑圈里,听她给我们讲各种当时英语课本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奇故事。 我们的听觉神经像拉满了弓一样绷得紧紧的,因为听了两遍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她的要求,把故事一一重复一遍。 她的评判标准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看我们是否理解并记住了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二是看我们使用的单词、句子、语法是否正确、得体。 就这样,我们用自己的破烂漏洞百出的英语句子毁了她的好故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常常在复述一个故事后满头大汗。 渐渐地,挡住我们的黑墙打开了。 那些开口的周围,都出现了裂缝,裂缝如藤蔓般延伸学英语有哪些困难,缠绕在一起。 终于有一天学英语有哪些困难,所有的洞都串通了,墙倒塌了,我们走到了墙的另一边。 我们发现我们的英语不再只是我们的头脑和眼睛,它也成为了我们的耳朵和嘴巴。 它也是脚,引领我们进入别人的世界。 它甚至是一只手,引导我们敲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大门。
周老师的教学特点可以用两个成语来概括:循循善诱、怒中忍耐。 前者指方法,后者指姿势。 即使她背对着你,她的眼里也总是闪烁着权威的光芒。 学生中那些顽固或偷懒的人,常常会被她无情地斥责。 几十年后回想那段经历,对女王陛下的恐惧早已消散。 现在我想起来都很感激,因为她教会了我一种学习方法,并且我把它推广到了其他语言。 几乎在所有的学习过程中。 后来它几乎成了我的生活态度,我用它来抵制各种模糊和模糊。
周老师虽然靠私下辅导学生为生,但她并不收太多的学生。 她衡量一个学生是否可教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学生的汉语水平。 她认为,汉语基础扎实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语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在她看来,母语是一切语言的基础,任何外语都只是从母语的基础上拔出的树枝和果实。 根厚则枝繁;根厚则枝繁;根厚则枝繁。 根浅则枝枯。 基于这个原则,她录取了一名英语成绩只有十几分,但汉语基础扎实的学生。 这位大三学生考入了北大西班牙语系,成为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传奇人物。 许多年后,我偶然在海外看到了徐志摩、张爱玲的英文日记和散文。 他们的第二语言叙述中的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两个没有接受过系统英语文学训练的人之所以能在非母语叙事中绽放出如此茂盛的花朵,其实是因为他们在母语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根基。 。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周老师如此重视我们语文能力的深意。
1979年,我用中学围墙外学到的英语打开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门。 精英学校的新一轮审查——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另一个故事了。 我把我的英语比作一件衣服。 我求学期间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在那件衣服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我已经分不清哪一块布是何丽达的,哪一块针线是前联合国雇员或前教会学校老师的,哪一块针线是周老师的……我走在大观里第二语言花园穿着这样的百针衣服。 我感到自卑和骄傲。
当年对一门外语单纯的好奇心,至今似乎也没有完全消失。 这些天,我经常环游欧洲大陆。 每当我经过一个不懂语言的城市时,我都会悄悄地问自己:今天,我是否有兴趣缝制另一件可能被称为法国、德国或荷兰的作品? 白聂伊? 我还能有同样的耐心和勇气去面对那漫长而快乐的过程吗? 我会遇到另一个何利达或者另一个周老师吗?
或许。 我告诉自己。
本文摘自《曾经辉煌的废墟》,张岭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本文由佚名发布,不代表阿卡索英语培训 - 英语一对一线上外教培训!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ydy/12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