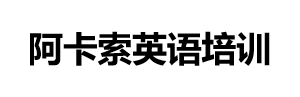拉丁外教一对一 徐世成:我愿做拉美研究的“春蚕”
受访人:徐世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记者:万代
受访者简介:徐世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1964年至1967年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史学院进修。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拉美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出版有《碰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1999年)、《古巴民族》(2003年)、《拉丁美洲政治》(2006年)、《卡斯特罗批判传记》(2008年)、《查韦斯传记》 》(2011)等多部学术专着,翻译《第三次革命》(1999)、《游击队时代》(2015)等多部著作,主编《拉丁美洲史(第二卷)》(合编) )(1993)、《帝国霸权与拉美——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预》(2002)、《美国与拉美关系史》(2007)等多部学术著作或文集。曾获古巴**、古巴拉美通讯社“友谊奖”、建国50周年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他是我国拉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研究内容涵盖拉丁美洲研究的各个领域。他被拉丁美洲研究的学生称为“徐老师”。他是中国拉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拉美研究多个学科的带头人。作为这一方向的先驱,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撰写和出版大量书籍。他深入研究拉美左翼和古巴问题,半个世纪不变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和忠诚。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成。
日前,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资深学者,了解并分享了他的学术生活以及他对拉美研究的经历和思考。
西班牙语学习“从俄罗斯到西方”
万代:您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西班牙语、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之一。您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您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背景,以及您是如何走上拉丁美洲研究道路的?
许世成:1959年我在上海高中毕业后,首先被选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预科,准备派往苏联留学。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减少了我公派留学生的数量,此行未能成行。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去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迎新实习生。当时,北京大学刚刚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还是第一届。与我同去北京大学的还有苏振兴(后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拉美研究所所长)、史瑞元等人。 1961年,拉美研究所成立时,我们被告知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美研究所工作。
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习条件并不像现在这样。前两年,没有西班牙语词典,也没有课外读物。当时,北大西班牙语系只有一本西班牙语杂志《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放在教师阅览室。大多数学生不让进去,我只好想办法去老师阅览室看。老师的阅览室里还有一本日本出版的西日词典。虽然我不懂日语,但是日语里有很多汉字,所以我在字典里猜了一些西班牙语短语。第三年,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西汉词典(周恩来**题词),我再也不用猜西日词典了。
我们的外教只有三年级。最初,我们的西班牙语老师是菲律宾华侨周素莲。周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英语系。菲律宾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她懂一点西班牙语。两位法国老师教我们西班牙语语法。他们一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西班牙语课,一边教我们。三年级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些来自拉丁美洲的外教,包括来自阿根廷、巴拉圭,后来又来自乌拉圭。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我们班18个学生有18种不同的发音。
从革命沃土出发的拉美研究之路
万代:当时的学习条件相当艰苦。不过,正如赵德明老师在我们采访中所说,服从国家的需要,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信念。后来组织送你去古巴留学,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许世成:我们几个人之所以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是因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0年与古巴建交后,我们需要懂西班牙语的干部、翻译和研究人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仅要研究非洲,还要研究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于是中国科学院同时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东欧和东南亚研究所。这四个研究所均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1964年1月,我作为教育部派遣的留学生赴古巴学习。那时我就知道我回来后要从事拉美研究。 5月,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熙访问古巴。他告诉我,拉美研究所和另外三个地区性研究所划归中联部管辖。
万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去古巴留学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许世成:我去古巴留学的目的比较明确,选修课也比较有针对性。在第一年,您必须首先提高西班牙语水平。虽然我已经在北大学习近四年了,但提高西班牙语仍然是我的主要任务,因为我将来要从事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在第一年,我除了选修语言课程外,还选修了所有与古巴相关的课程,比如古巴外交、古巴历史、古巴文学甚至古巴地理。第二年我主要选择了西班牙语相关的课程,比如西班牙历史、西班牙文学等,因为要了解拉丁美洲,首先要了解西班牙。第三年,我选择的课程更加宏观,包括拉美历史、拉美政治、拉美文学等。我还选修了托雷斯教授的《拉美的不发达与殖民主义》等课程,时任古巴**副部长。总之,我基本上参加了哈瓦那大学开设的所有拉丁美洲课程。当时古巴正处于革命胜利初期,不少拉美进步人士避难古巴。比如,给我们讲授拉丁美洲古代历史和当时玛雅文明的老师曼努埃尔·加利奇,他是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府时期的**长,也是“危地马拉众议院”首任主席。美洲”。 1960年访华。他关于玛雅文明的课程非常生动,危地马拉是玛雅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给我们讲授拉丁美洲近代史的老师是时任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担任古巴**副部长、部长、全国人大主席的里卡多·阿拉尔孔·德克萨达。教我们拉丁美洲文学史的人是来自多米尼加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教授,名叫卡米拉·恩里克斯·乌雷尼亚(Camila Enriquez Ureña)。
我就读于哈瓦那大学文学与历史学院(现更名为文学艺术系)。和我同年级的还有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在哈瓦那大学的三年里,我收获了很多。我们不仅学习书本知识,还参加劳动,进行社会调查。我们在古巴的三年里,每年夏天甘蔗季节(古巴称为“糖季”)我们都会砍甘蔗。第一年是为他的农场里的一个小农砍甘蔗。其实,小农并不小,土地也很多。古巴土地改革后,规定小农可以拥有5个caballeria(古巴土地计量单位,共13.43公顷),加起来就有几千英亩的土地。第二年在合作社度过,第三年在国营农场度过。由于1965年后中古关系恶化,使馆研究室的同志无法离开。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后来驻秘鲁大使的杨迈要我们帮助使馆进行调查,了解古巴农村是什么样子,小农户、合作社和国有农场发生了什么,然后写出来一份报告。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和古巴农民、合作社成员、学生聊天,写了一份关于古巴土改后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小农、合作社成员、农场工人的收入等的研究报告。由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转交教育部并在其内部通讯上公布。
万代:当时在古巴留学的中国人多吗?留学生活丰富多彩吗?
徐世成:当时有两批留学生。一组高中毕业,来到古巴学习。我们被称为“小同学”,独自生活在古巴的一个地区。另一组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包括**大使黄志良(曾为毛主席做翻译),还有我们几个应届毕业生。在这些老同志的帮助下,我们不仅学习了这些年在古巴的书本知识,还了解了古巴革命、古巴农村的情况,还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 1964年,古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还和古巴大学生一起进入军营,在古巴西部的部队里呆了三个星期,帮助挖战壕。古巴革命初期,曾开展过各种声援活动。 “美洲之家”每年经常邀请许多拉美著名作家举办文学比赛,大家喝咖啡、听报告。当时的记者包括专职作家和拉美政坛知名人士,如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国的游击队指挥官。当时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经常去美洲之家等地听讲座、参加活动,增加对古巴和拉丁美洲的了解。
徐世成:是的。有一次,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崔鸿儒老师到古巴工业部参加支援越南的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工业部长切·格瓦拉主持。我和崔鸿儒坐在后排。会议结束时,格瓦拉以为我们是越南学生,就把我们叫过去聊了一会成。我们说我们是中国学生,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因为他两次访问中国,并谈到了他访问中国的想法。许多年后,我访问了古巴,参观了几位因研究格瓦拉而闻名的学者的家。他们的家就像一个格瓦拉博物馆,里面有很多格瓦拉的画作和书籍。但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都没有见过格瓦拉,但我有幸见到了格瓦拉本人。所以我在古巴的三年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实践与研究:从欧洲到拉丁美洲
万代: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您回国后开始从事拉美研究吗?

许世成:我是1967年2月回国的,回国后先派我陪同西班牙左派代表团访华四个多月。后来,他被派往广东牛田洋陆军农场受训,又从陆军农场到河南**国际部五七干校,在那里待了半年。年。 5月7日从干校回来后,我正式分配到**对外联络部拉美司(后改为拉美局)工作。当时,耿飚担任**对外联络部部长。他此前曾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公使说,驻阿富汗使馆需要一名懂西班牙语的干部,所以领导安排我到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等国的左翼人士访问阿富汗。从1972年2月到1976年7月,唐山地震前一天我回国,我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工作了四年多。
万代:虽然您这几年的工作不涉及拉美研究,但确实涉及拉美外交。可以说,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做了铺垫?
徐世成:可以这么说。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后,拉美地区正准备复苏。研究所领导王康到避震避难所看望我。他告诉我,你是我们拉美研究所修复筹备组领导班子的成员。 1976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重建,我成为研究所领导班子成员和南美研究室(当时称南美研究组)主任。后来苏振兴从阿根廷大使馆回来后,我们原来的南美调研组就分成了两部分。我负责研究安第斯山脉国家,也可以说是上南美洲;苏老师负责研究南美洲南部地区,即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拉丁外教一对一 徐世成:我愿做拉美研究的“春蚕”,他担任南美洲下游集团的领导者。
万代:“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一切都等待着去做。我们应该如何开始研究工作?
徐世成:我是从安第斯国家开始研究拉丁美洲的。我当时是拉美研究所的研究员,访问拉美国家的次数比较多。 1979年5月,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当时,哥伦比亚尚未与中国建交。我们受到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阿亚拉的接见。我问总统哥伦比亚何时与中国建交。总统还半开玩笑半正式地说,当中国购买我们的咖啡时。半年多后,1980年初,总统兑现了承诺:哥伦比亚与中国建交,中国也开始采购哥伦比亚咖啡。你看,哥伦比亚咖啡现在在北京的星巴克和超市都有售。此外,还有来自巴西的咖啡、来自中美洲如萨尔瓦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咖啡。
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访问拉美的全国友协代表团。回国后,我被要求为西班牙版《中国建设》写一篇《访问拉美国家》的文章。这是该杂志的第一篇西班牙语专题。我后来写了《安第斯条约组织发展趋势》一文,因为我访问秘鲁时参观了安第斯条约组织(现称安第斯共同体)总部。我可能是第一个访问安第斯条约组织的中国人,他们也在出版物上专门报道了我的访问。我写过几篇有关安第斯条约组织和安第斯五个国家历史的文章。同时我还写了一些其他关于安第斯国家的文章,比如智利为什么退出安第斯条约组织,玻利维亚的出海问题等。
万代:您后来参与了国内学者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拉丁美洲通史——《拉丁美洲史》的撰写。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创性。能谈谈写作过程和当时的一些想法吗?
徐世成:是这样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李春晖教授写了一部拉丁美洲通史,题为《拉丁美洲史手稿》,商务印书馆于1983年出版。但这部著作只写了世界大战后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古巴革命)。于是,他邀请我和苏振兴先生等人参与拉丁美洲近代史的撰写。随后,在李春晖的带领下,我和苏振兴三人一起编辑了《拉丁美洲史手稿》的现代部分。当时是《拉丁美洲史手稿》的第三卷,现在是第二卷。在决定继续撰写这部历史手稿的近代史部分后,编委会组织作者在双清山庄召开了编辑会议拉丁外教一对一,讨论了第三卷的结构和内容安排。他们还特意邀请了**对外联络部拉美局副局长杨白冰等出席会议。当时会议住宿条件非常简陋,连抽水马桶都没有,这对于李春晖教授等几位老学者来说非常困难。但与会学者仍保持着极大的热情,通过多次会议成功确定了第三卷的大纲和工作安排。依托拉美学院当时国内最齐全的中外文资料,苏老师负责了本书的综合部分。在这本书中,我介绍了四个安第斯国家(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后来又添加了尼加拉瓜。这是关于书写五个国家的近代史,很多专家参与了书写。这本拉美历史书对全国普及拉美相关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后来我被调到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室。 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外教一对一,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所以我专门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拉美经济问题。当时我买了很多专业书籍。我大学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补课,尤其是一些西方经济理论的书,包括美国人保罗·萨缪尔森写的书。另外,我还开始学习拉美国际关系。就这样,我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开始延伸到很多领域。
古巴情怀:贫穷和卑微无法动摇,权力不能放弃
万达:您的留学经历,甚至您的学术生活,从起源到结果都与古巴息息相关。您也是古巴问题的权威专家。这个加勒比国家在你们的学术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您的专着包括《碰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民族国家:古巴》和《卡斯特罗批判传记》。 ”等,翻译作品有《蒙卡达的审判》、《时代游击队》、《马蒂诗选》(合译)等。您认为,您的留学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您对古巴有什么学术研究吗?
许世成:古巴留学对我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到达古巴时才22岁,那时我的世界观正在形成。我到达古巴时,也正值古巴革命胜利初期。当时,古巴人民的革命热情高涨,尤其是大学生:大家经常光着膀子帮助农民砍甘蔗、义务劳动。我们这群国际学生和后面的群体略有不同:我们和古巴人、其他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住在同一栋公共建筑里,而我住在16楼。大楼里经常会有评估和健康检查,也经常会发生一些争论。这还有利于锻炼你的听力技巧。刚到公立学生楼时,我经常听不懂电梯里古巴人使用的俚语。它不仅是古巴人互相开玩笑时使用的俚语,甚至当他们问我“你习惯在古巴生活吗?”时,他们也没有使用通常的西班牙语“Acostumbrado”,而是“Aplantanado”,这是源自西班牙语单词“Acostumbrado”。源自“香蕉”一词。我们一行人与古巴人和拉丁美洲人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参加活动。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还一起去山上挖战壕。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由于古巴客观条件的限制,后来的留学生一般都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网络资源,这些都是古巴紧缺的。据我了解,古巴当地学生需要根据年级和专业去专门的机房上网,但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就方便多了。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失去了一些与古巴学生同甘共苦的经历。
万代:这样的人生经历确实非常宝贵。那么,在思想层面呢?
许世成:从思想上来说,古巴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几年前,一位博士生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的多位学者,问我们“我们敬佩的英雄是谁?”我当时的回答是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与白求恩有些相似:他是阿根廷人,家庭环境富裕,父母都很富有。电影《摩托车日记》还介绍,格瓦拉年轻时曾骑着摩托车游历美洲大陆,前往秘鲁调查穷人的生活和麻风病人的状况;经历过危地马拉革命;后来来到墨西哥并在墨西哥城工作。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人们以摄影师的身份赚钱。后来他遇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把他介绍给了他的兄弟菲德尔·卡斯特罗。经过一夜的长谈,格瓦拉愉快地加入了墨西哥的古巴革命队伍,乘坐“格拉玛”号前往古巴,并在马埃斯特拉山区与游击队作战(尽管他本人患有严重的哮喘,但他仍然坚持在古巴革命的前线)。斗争)。我有幸在古巴与格瓦拉见面并交谈。那时我经常听他的演讲。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古巴拉丁外教一对一,这让这次交流变得更加珍贵。格瓦拉为了拉美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无愧于英雄之名: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美国面前,经受住了经济封锁、政治压力、军事渗透甚至多达六七百人的迫害。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倍。暗杀行动始终坚定不移。
应该说,现在回想起来,原来的古巴革命和古巴革命的英雄们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不在亚洲的就是古巴。古巴历史上虽然有过亲苏时期,但由于对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导致中古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但作为领导人,卡斯特罗对苏联的局势有着清晰的预见。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古巴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点。 。我国历代领导人都与古巴保持着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去世时,**主席不仅发来唁电,还亲自前往古巴驻华使馆表示哀悼。习主席在唁电中高度评价卡斯特罗。他认为卡斯特罗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是中国人民的亲密同志和真诚朋友。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是卡斯特罗在没有任何事先谈判的情况下在数百万人面前宣布的;卡斯特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说古巴一直对我影响深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富不能淫、贫不能移、权不能徇”的伟大国家。无论是切格瓦拉还是卡斯特罗,他们确实是革命者学习的榜样。受此影响,我的学术研究一直以古巴为重点,包括花费大量精力撰写《卡斯特罗传》等一系列作品。直到今年,我还写了一些有关古巴的新文章,重点关注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革、修改宪法等问题。
拉美左翼研究:微观层面左退右进,宏观缓慢兴盛
万达:同样,您也对拉美左派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书籍,例如《拉美左派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复兴》等。 《古巴模式与拉丁美洲左派的崛起》、《拉丁美洲的现代思潮》等,您是如何开始并将这部分研究作为重点的?
许世成:对拉美左派的研究也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我们聊了。我曾经在阿尔巴尼亚使馆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拉丁美洲和各国的左派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了欧洲,放弃了革命理想;还有一些人为祖国的革命事业献身,甚至献出生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拉美研究领域后,我继续关注和研究拉美左派。
近年来,我多次受邀参加拉美左翼论坛,如墨西哥民主革命党组织的民主左翼会议,邀请了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作为国际观察员,我应邀前往委内瑞拉观察其议会和总统选举。 2016年,他还参加了支持委内瑞拉日的左翼集会。由于委内瑞拉执政党、联合社会党和政府邀请各国左翼分子,我也有机会接触到秘鲁等拉美地区的左翼政党领导人,包括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以及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万达:您如何看待当前拉美局势以及拉美左翼的未来走向?
许世成:我认为过去一二十年,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但拉美是世界上唯一左翼势力明显崛起的地区。从21世纪头十年至今,拉美左翼政权和政党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2018年,墨西哥左翼民族复兴运动党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赢得大选,这意味着墨西哥历史上首次由中左翼执政。在2019年10月27日的阿根廷大选中,中左派佩隆主义党总统候选人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击败了总统毛里西奥·麦克里(Mauricio Macri),这意味着阿根廷左翼重新上台。但是,在2019年11月10日拉丁外教一对一,在拉丁美洲重要的左翼国家玻利维亚发生了一次政变。莫拉莱斯总统被迫辞职,并在墨西哥流放,这对拉丁美洲的左派造成了严重打击。拉丁美洲的当前状况是左右之间的游戏,双方都赢了或输了。随着乌拉圭选举的结束,中右民族党的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勒·普(Luis Lacalle Pou)击败了左翼统治联盟广阔的阵线,这在整个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左右进步。
无论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左派仍然是世界主要地区之间相对强大的力量。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古巴是亚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和危险,并且仍在西半球。这是拉丁美洲左派发展的主要刺激。此外,拉丁美洲还拥有圣保罗论坛,这不仅是拉丁美洲左派的论坛,而且还具有全球影响力(邀请欧洲和亚洲的左派政党,包括我的国家,也应参与)。最近,由大约20名现任和前拉丁美洲政治家组成的中左中心集团,包括阿根廷总统当选费尔南德斯,墨西哥总统洛佩兹和前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Correa)。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拉丁美洲的新兴力量离开了。因此,我认为,作为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我们应该关注拉丁美洲左派的发展,并注意拉丁美洲左派的趋势。在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缓慢的繁荣时期。拉丁美洲左翼的持续发展是这种繁荣的明显证据之一。
本文由佚名发布,不代表阿卡索英语培训 - 英语一对一线上外教培训!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peixun/19840.html